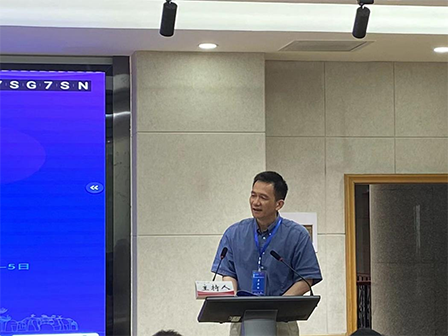纳粹统治下的哥廷根数学
观点 · 2009-06-02 00:00
返回1931年的哥廷根数学研究所(the Mathematical Institute in Gottingen)有着杰出的学术传统:从高斯,黎曼,狄利克莱,到菲利士·克莱因(Felix Klein),闵可夫斯基和希尔伯特。研究所坐落在一栋宽敞的新大楼里(还要多谢洛克菲勒基金会,...
1931年的哥廷根数学研究所(the Mathematical Institute in Gottingen)有着杰出的学术传统:从高斯,黎曼,狄利克莱,到菲利士·克莱因(Felix Klein),闵可夫斯基和希尔伯特。研究所坐落在一栋宽敞的新大楼里(还要多谢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巴黎也盖了这么一栋给数学研究用的大厦),里面的图书馆十分宽敞,而且保存了一篇关于方体填充问题的著名论文,其中用尺规给出了一个清楚的构造
。它的师资队伍数量不多(按现在的标准而言),但是质量是超群的,还包括了大批青年人。
在我那个时代以前,许多美国数学家(最近的有H. B. 卡瑞(H. B. Curry))曾在哥廷根留学过。在这篇文章里我会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并用一定的篇幅引用我当时(1933年)写的一些信,因为这些信件记录下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1931年的时候我已经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了茫然而失望的一年研究生生活,我那时在找一所真正一流的数学研究所,还得包括数理逻辑方向,而哥廷根则兼具这两者。
当时希尔伯特已经从教授岗位上退休了,但他还每周作一次名为“基于现代科学的哲学简介”的讲座。接替他的赫曼·魏尔(Hermann Weyl)广泛地教授微分几何,代数拓扑和数学哲学(我记下了这一门课的讲稿)。从他的群表示论研究班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方说运用线性变换),但我没有听从他说的代数家应该研究李代数的结构的主张。我也没有被他下的一个结论——集合论里涉及了太多的“沙子”所说服。埃德蒙·兰道(Edmund Landau,1909年起为教授)用他所习惯的精
炼清晰的方法给大量听众上课——同时还得用一个助手来帮他用水擦洗用过的(滚动)黑板。研究所的行政领导理查·科朗(Richard Courant)讲授并调度许多助手处理科朗-希尔伯特文集(the Courant - Hilbert Book)的手稿。G·赫格罗茨(Gustav Herglotz)在很广泛的课题上——李群,力学,几何光学和具有正实部的函数——雄辩地作他深刻的讲座。菲利士·伯恩斯坦(Felix Bernstein)教统计,但是他在1932年十二月,动荡还没来临之前就离开了。这些就是当时哥廷根的
正教授(ordentliche Professoren)了。
副教授(ausserordentliche Professoren,声望差多了)包括保罗·伯尔内斯(Paul Bernays),保罗·赫尔茨(Paul Hertz),埃米·诺瑟尔(Emmy Noether)。赫尔茨讲授因果律与物理(拥有马克斯·波恩(Max Born),理查·坡尔(Richard Pohl),詹姆斯·弗朗克(James Franck)的著名的物理研究所就在隔壁)。伯尔内斯跟希尔伯特一起搞逻辑学,那时正在准备出预计中的希尔伯特-伯尔内斯文集《数学基础(Grundlagen der Mathematik)》。他还(不那么热情地)教有名的菲利士·克莱因的高起点基础数学课(主要面向未来的体育老师)。
埃米·诺瑟尔(魏尔说她比得上他)十分热情但有点含混地教和她那时的研究方向相同的课程,也就是群表示论和代数论。她的桃李中包括恩斯特·维特(Ernst Witt)和奥斯瓦尔德·泰西穆勒(Oswald Teichmuler)。
还有一些年轻的讲师(Privatdozenten,直译是“私职教师”不过在德国是公职)和助教(Assistenten),包括汉斯·卢威(Hans Lewy),我从他那里学过偏微分方程,奥托·诺伊格保尔(Otto Neugebauer,数学史),阿诺德·施密特(Arnold Schmidt, 逻辑),还有赫尔伯特·布瑟曼(Herbert Busemann),乌尔纳·芬切尔(Werner Fenchel),弗朗茨·雷利希(Franz Rellich)和威廉·马格内斯(Wilhelm Magnus)。我们常常跑到附近火车站旁一家不错的馆子里,边吃饭边讨论。那时有不少很有求知欲的学生,包括格哈德·根岑(Gerhard Gentzen,逻辑),福里茨·约翰(Fritz John),彼得·舍克(Peter Scherk),奥尔加·陶斯基(Olga Taussky)和恩斯特·维特(Ernst
Witt)。
社交活动包括在魏尔教授家不时举行的舞会。如果在一个星期天你光临了埃德蒙·兰道华丽的豪宅,并且留下了名片,那这肯定会让兰道教授办派对并邀请你参加,派对上还会有很多对抗性的游戏可玩。有一次,兰道邀请G. H. 哈代(G. H.Hardy, 英国数学家)来访问。兰道到火车站去接他,哈代穿着一件宽大的军用雨衣,带着墨镜从他的车厢里走了出来。兰道冲过去见他,一边不忘问他在解析数论上用的“小弧(minor arc)”的最新成果;让兰道失望的是,哈代回答说他已经对此完全没有兴致了。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墨镜遮掩的不是哈代,而是兰道的一个很喜欢开玩笑的学生。
还有很多其他的访问者:保罗·亚力山德洛夫(Paul Alexandroff)曾经来作过关于代数拓扑最新阐述的报告(收在他精炼的著作《(代数拓扑)基本概念(Einfachste Grundbegriffe)》里),埃米尔·亚丁(Emil Artin)从汉堡来解释域类论朦胧的美,奥斯瓦尔德·费布伦(Oswald Veblen)(在一次每周例行的专题报告会上)讲授射影相对论理论。在这种专题报告会之前总是还有茶会和最新期刊的展示。理查·冯·密瑟斯(Richard Von Mises)当时是柏林大学(哥廷根的老对手)的教授,他作过一个(有一点含糊的)基于他的“Kollektiv”概念的概率论基础的晚间报告会。哥廷根的全体同仁都来听了他的报告,然后(希尔伯特,伯尔内斯,伯恩斯坦和其他一些人)致欢迎辞。简而言之,人们在激烈地交流和讨论新思想。那里还有许多个人的联络,比方说,有一段时间我住在科朗的家里教他英语,他那时正准备去美国访问。
1931-1932年的哥廷根数学研究所就是这么一个生机勃勃,成功的顶级数学研究中心的典范。
1931年德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大萧条使德国产生了大批失业者,而且许多德国人还对战后痛苦的通货膨胀记忆犹新。当时的德国总理(布吕宁,Bruning)在国民议会里并没有取得绝对多数,所以他只是依据紧急状态法统治。我认识的人当时都在关注这件事,而且大多同情自由派或者说左翼,但我记得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见后来发生的事。我到德国的第一站是柏林,我去那里学习德语和接受文化熏陶,比方说伯尔托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 德国诗人,剧作家和左翼戏剧改革家)和他的“三分钱歌剧(Drei Groschen Oper)”。在那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与纳粹冲锋队(德文是Sturm Abteilung,英文叫Nazi Storm Troopers,简称SA)竞争。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本名为《德国的二十七个政党》的小册子,当时魏玛共和国已经把政治肢解得不成样子了。
我在哥廷根一安顿下来,每个星期天就可以看到那些头上缠着绷带的年轻学生——这是在“颜色”学生军团(原文为"color" (corps) fraternities)练习对打时留下的,也许他们在期待大家对炫耀对打时留下的伤疤的法律系教授肃然起敬吧。有一次在冬天,我还保护过一个没头没脑朝某个学生军团团员扔了一个雪球的街边流浪儿。那个学生因此就上来找碴:“你的名片?”我当时没有带,所以就回绝了。然后那个学生就说:“Mit solchen Leuten verkehren wir nicht!”——我们不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他后来果真没有怎么跟我打交道,在街上碰到我他总是带着无言的蔑视走开。我可能算是走运的,马丁·科内瑟尔(Martin Kneser)告诉过我1912年乔治·坡利亚(George Polya)在哥廷根也被学生这么挑衅过,然后他回绝了,结果是院长建议他离开学校。我还是决定留下来,这使我受益非浅。
1932年德国政治一片混乱,在柏林和外地还有纳粹冲锋队和共产党的街头暴力冲突。然后在1933年的一月举行了一次大选,纳粹和德国国家党(German National party,由冯·帕朋(Von Papen)领导)联合取得了议会多数,这些国家主义者们当时可能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希特勒吧。加起来的选票足够使希特勒获得总理一职了,当时他的讲话和画像随处可见。
1933年二月十二号,我趁假期访问了魏玛。一到那里我就直扑歌剧院,然而第二天的票已告售罄(那时正是瓦格纳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万幸的是,我第二天早上就来歌剧院门口站着,终于搞到了一张票。上半场(当然是瓦格纳了)演出非常华丽。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信步走到了门厅,在那里,二十五呎远的地方站着希特勒和戈林(很容易通过他们在报纸上的照片认出来)。那时我还没有(象我几个月以后那样)意识到邪恶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在以后的几年里,我还清晰地记得见到希特勒的那一幕,但一直以为时间要晚一点,是在1933年的五月份。后来我总觉得那是一次机会,一次我可以亲手改变历史的一次机会(假如我当时带了武器的话)。
1933年三月五号,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之后,联合政府举行了第二轮选举。这让政府得到了多得多的选票。我在给我妈妈写的两封信中描述了之后的局势,这两封信一封落款为1933年三月十号,另一封则没有记下时间(作者可以根据请求提供这两封信)。
第一封信(10.III.33)是好笑地吹捧政治宣传的。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官方的宣传可以如此地改变民众的立场。在我八月份离开德国的时候,我才觉出我已经被愚弄得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了。
在第二封没有日期的信中(“地址被省去”),我好像在担心我的信可能会被审查。现在我认为这种担心没什么根据,但是我当时真有点惦记我那份《资本论》(Das kapital),我记得我把它小心地放在了一个抽屉里,上面还盖着几件衬衣。实际上在1933年三月十号哥廷根的确搞过一次焚书。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妈妈给我寄的几份文艺文摘(Literary Digest)也没让邮来。
写了那两封信之后,我参加了学生组织的两个星期的滑雪旅行,目的地是在图罗(Tylor)的奥博斯特多夫(Oberstdorf)。我们坐火车(团体票)回来时在纽伦堡(Nurenberg)停了三个小时。那正是希特勒公告和平抵制所有犹太商店的当天。我把滑雪板和行李放在火车上,然后就去镇子上逛。在一个很大的鞋店前我看到有一个仪表不怎么整洁的人在窥视橱窗。商店已经关门了,但警察还是发现了这个人,然后推推搡搡地把他弄走了。因为我认为这次经济制裁应该是非暴力的,所以就很好奇地跟上去看。马上我也被逮捕了。认真的警察一口咬定我是一个盎格鲁-萨克逊记者,训斥我企图收集对元首不利的谣言。我努力让他相信,我不是记者而只是一个(来旅游的)学生,跟着他就说,如果他在美国旅游他就不会去惹警察。我用尽浑身解数交代,我的所有随身财产都在火车上,而火车就要开走了——我最后被放了,时间刚刚好让我赶上车。我又回到了洛策路二十八号(28 Lotze Strasse, 离数学所不远),我在哥廷根住的地方。那里的房东经常招待我喝晚茶,一起聊天。我一下子就发现,两个星期的政治宣传已经把她从温和的保守派变成了一个狂热的纳粹信徒。
在德国,教授,讲师和助教都是政府公职。然而1933年四月七号颁布了一条新的法律:除了1914年以前聘用的和曾经参加过一次世界大战的以外,所有犹太教授全部就地解雇。这还不算,还有那些“没有全心全意维护国家社会主义祖国的公职人员”也将要被扫地出门。
数学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朗,诺瑟尔和伯恩斯坦立刻被解雇了(时间是四月二十五号),拿科朗来说吧,他参加过一战的经历也没有帮上忙,这显然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和他在数学界的影响力(继承自菲利士·克莱因)让某些人不高兴了。他走后诺伊格保尔成了所里事实上的一把手,然而他才坐了一天位子,自己就也被解雇了,原因明摆着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同情心,不过也许是他没有修整他家的草地!四月二十七号,伯尔内斯,赫尔茨和卢威被解雇。有人告诉兰道,接下来的夏季学期他不必教课了,兰道也就照办了。这些事情让我在五月三号给我妈的信中写下(部分):
“由于这么多教师都被开除或者主动离开,数学系基本上废掉了,现在搞数学很难。我们也只能或多或少地安慰一下自己说对德国人民而言这好极了吧。”
接下来的夏季学期,一切都在艰难地挣扎。所有来得及毕业的学生都在赶紧对付毕业必需的东西。我没有了我的论文导师(保罗·伯尔内斯),魏尔接替了他,以后他给了我一次相当难的口试。我倒是通过了,但是在问到Hausdorff空间的定义的时候,我忘记了分离性公理,当时也不敢提其实魏尔本人有一次在他的作品中也忘记了。另外一次口试的内容是莫利茨·盖格尔(Moritz Geiger)教授给我上的数学哲学课。虽然他是犹太人,可他参加过一战,所以还算是留了下来。但每一节课我都注意到他对未来的紧张和焦虑,实实在在的焦虑。
六月十四号,我跟我妈写信提道:
“就在最近有消息说德国的革命要结束了,现在什么事情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来一步步改良。这似乎表明,到目前为止,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严格依法来办理的,或者说至少冲锋队有时就包揽了警察才能有的权力。具体搞成什么样子我也说不清楚。”
那时我的未婚妻多洛茜·琼斯(Dorothy Jones)已经从纽约来哥廷根帮我完成论文了。她也了解了不少政治局势。当我和她去办结婚证的时候,我们俩惊奇地发现我的学生弗里茨·约翰(Fritz John)和他的朋友夏洛特(Charlotte)也在。我们的在场让他们俩感到非常不安。小伙子是犹太人而姑娘不是,他们想尽早结婚因为弗里茨估计很快就会有法律禁止这种通婚了。我们答应替他们保密,而他们则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婚礼以后举行的宗教典礼(feierliches Abend)。在来宾中还有一位长金色头发的德国小伙子和他的一眼就能看出是犹太裔的女朋友。多洛茜后来给我妈写信说,“这样的婚礼浪漫中蕴藏着风险”。
七月二十五号我跟妈妈写道:
“政治还在象一直以来那样引人注目。星期五晚上我和多洛茜去听了一场关于在德国大学里建立新秩序的纳粹演讲。我们发现这可以算得上是最有理性的一场了。演讲人(柏林一位出名的纳粹教授)没有要求科研完全为政治所约束。他说科研应该独立但不是自成一体…… 会后我们去了城里和我的朋友格巴特(Gebhardt)(我们早上碰到的)一起喝咖啡。我们在那里又谈论了政治,像天主教义(盲从)对希特勒主义的影响,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直到夜里。最近我注意到纳粹运动内部的立场很不一致。并不是每一个纳粹党人都有一样的想法,虽然这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1995年原注:我再也记不起关于天主教义的讨论了,那时我对德国天主教基本上是完全的无知。我还是我祖父富于感染力的偏好宽容的布道的忠实崇拜者。)
我还是担心我的口试——可怕的赫格罗茨教授的几何函数论。我去找有经验的朋友出点子,他们提示我他喜欢说教。这一点我在口试中记住了:
赫格罗茨:什么是Erlanger Program?
我:一切取决于群。
赫格罗茨:复分析的群是什么?
我:保形群。
这就足够让赫格罗茨教授开始一场几何函数论中的保形群的精彩讲座了。
我的答辩算是结束了,我完成了学业。
但对所里来说,损失还在增加。魏尔不是犹太人,但他的妻子是,这样他的两个儿子就都算是犹太人(是否算犹太人要看母系)。所以1933年夏季学期一结束,魏尔就为此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任教。算起来,1933年有十八位数学家自动离开或者被赶出哥廷根数学研究所,其中包括兰道,他虽然不算被正式解雇,但当他在1933年冬季学期重新教课时,学生们组织起来彻底地抵制了他的课。他于是投降,退休并去了柏林。
柏林大学的数学研究也中断了。他们损失了二十三位教师(包括理查·布劳尔(Richard Brauer),马克斯·邓(Max Dehn),汉斯·弗洛伊邓托(Hans Freudental),B. H. 诺伊曼(B. H. Neumann),汉娜·诺伊曼(Hanna Neumann)和理查·冯·密瑟斯(Richard Von Mises)在内)。别的德国大学所遭受的具体的(常常不很详尽的)影响已经在马克西米利安·平勒(Maximilian Pinl)的四篇文章中用表格仔细地列举了出来。肖帕切尔(Schappacher)曾在他的《纳粹统治下的哥廷根(Gottingen under the Nazis)》一书中对哥廷根当时的局势作过细致地分析。
有一个研究者这样总结数学研究所受的影响:
“就在几个星期里,这么多年来所创造的一切就被这场运动搞得烟消云散。一场人类文明自文艺复兴以来少有的惨痛悲剧就这么上演了——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能发生这样的悲剧,这在几年前是没有人敢相信的。”
曾经有过一些重建哥廷根数学研究的努力。著名代数学家赫尔姆特·哈瑟(Helmut Hasse)后来成为数学所的教授和所长,有一阵子他和几个热烈拥护纳粹的教授关系搞得很僵:奥斯瓦尔德·泰西穆勒,乌尔纳·韦伯(Werner Weber),爱德华·托尼尔(Edward Tornier)。托尼尔有段时间和哈瑟同为所长,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希望把哈瑟搞下台的。托尼尔支持党,比方说他后来曾在当时新办的《德国数学(Deutsche mathematik)》杂志1936年第一卷,第二页上写道(我的翻译——原注):
“纯粹数学也有实在的客体——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犹太自由化思想的代言人,就像哲学上的老滑头一样…… 一个纯粹数学定理有没有存在的权利要看它回答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涉及实实在在的物体,好比说整数或者几何形体,或者至少看它是不是为建构这样的东西而服务的。否则它就是不完整的,或者是从那些用没有客观根据的定义变戏法来误导他们自己和没头脑的群众的空想艺术家大脑里产生的犹太玄学的一个明证…… 将来,我们会拥有日耳曼数学的。”
最后哥廷根的四个教授职位又重新补满了(哈瑟,赫格罗茨,卡鲁扎(Kaluza),西格尔Siegel)),但即使是有了卡尔·路德维希·西格尔(Karl Ludwig Siegel),哥廷根往昔的荣耀也无法再现了。从某方面看,哈瑟曾想增加他对当局的影响力。据他的女婿马丁·科内瑟尔说,哈瑟为此曾申请入党,但后来人家发现他的一个祖母可能是犹太人,这样他的申请就这么一直拖到了战后。战争结束后,哈瑟又因为清扫纳粹的原因而被解雇。从那时起,哥廷根数学研究所和其他几所大学的类似研究所一起逐步地恢复,但它再也没有能重现当年那种光辉的主导地位了。
当我和多洛茜于1933年八月离开时,从前的哥廷根,独一无二的伟大的数学系典范已经珍藏在我心底。损失让我十分难过,然而我却不仅仅为科学而悲伤。我没能预见到大屠杀,但我的确意识到了国家机器宣传的威力,也真真切切地为一场世界大战的前景感到过恐慌,尽管我也知道我不可能阻止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这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场演示,一场任何对民众至上主义,政治压力和引导性的政治原则等的屈从对学术和数学生活的损害的无可置疑的演示。
参考书目:
[1] S. Mac Lane(1981). Mathematics at the Univeristy of Gottingen, 1931-1933, in Emmy Noether, A Tribute to Her Life and Work, (J. K. Brewer and M. K. Smith, eds.), Marcel-Dekker, New York, 1981, pp. 65-78.
[2] ___, Mathema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A Century of Mathematics in America, Vol. II, Amer. Math . Soc., Providence, RI, pp.128-151.
[3] M. Pinl, Kollegen in einer dunklem Zeit, Jahresber. Deutsch. Math.-Verein. 71 (1969), 167-288; (1970/71), 165-189; 73 (1971/72), 153-208;75 (1973/74), 160-208.
[4] N. Schappacher and E. Scholz, Oswald Teichmuller-Leben und Werke, Jahresber. Deutsch. Math. -Verein. 94 (1992), 1-35.
[5] N. Schappacher, Das mathematische Institut der Universitat Gottingen 1929-1950, Die Universitat Gottingen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Das Bedrangte Kapital ihrer 250-Jahrigen Geschichte, Munich K. G. Saur, 1987, pp. 345-373.
*********
说明:本文作者为美国数学家桑德斯·麦克莱恩(Saunders Mac Lane),原文(
Mathematics at Gottingen under the Nazis)发表于美国数学学会(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办的《Notice of AMS》上,编号是 Vol. 42, Number 10, 1134-1138. 如果想看原文可以去 http://www.ams.org/notices/199510/maclane.pdf 下载pdf文件。
文中大量运用括号作注解,其中除了人名和特别指出的以外均为原注。另外原文中的德语语音符号没有专门指出来,比方说哥廷根(Gottingen)中的“o”上面其实是有两点的。
因为水平所限,翻译中的错误肯定会有不少。而且为了语句通顺,本文基本上采用了意译,所以和原著在细节上一定会有不少出入。希望读者能够对比英文原文,不吝赐教。
原文网址:http://space.efnchina.com/user1/1267/10919.html